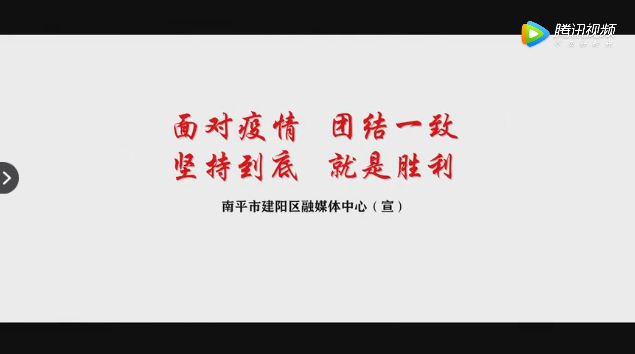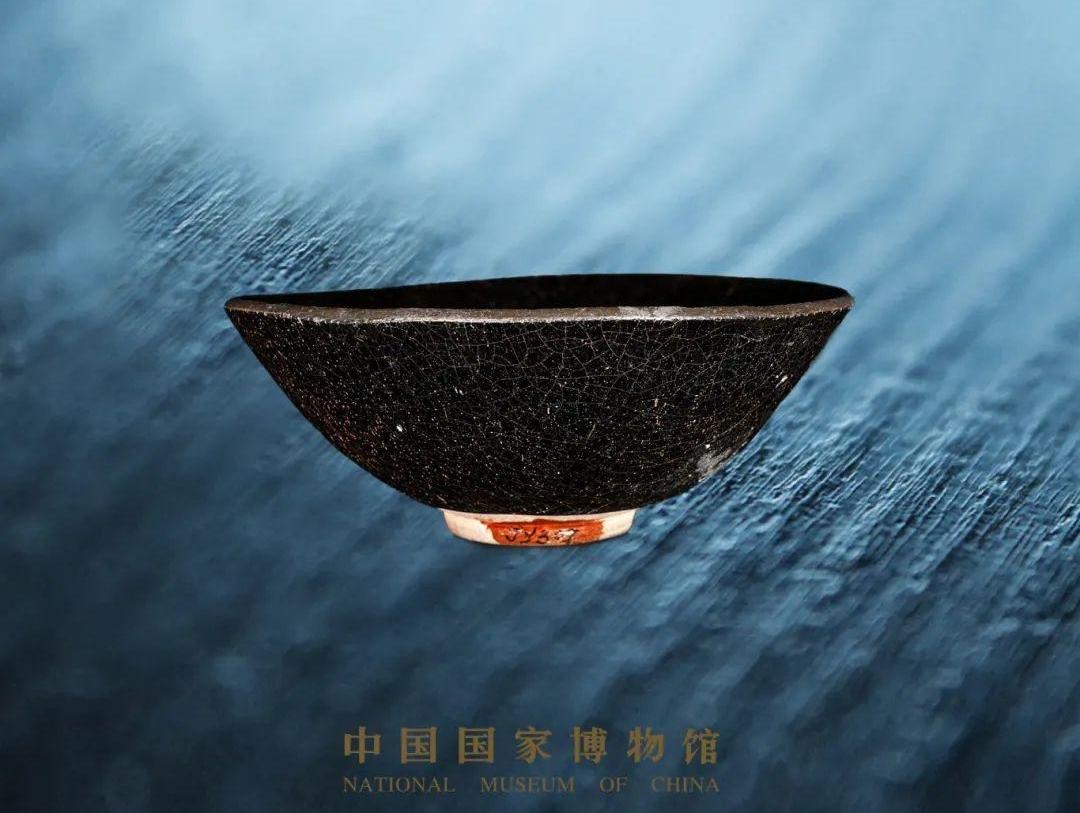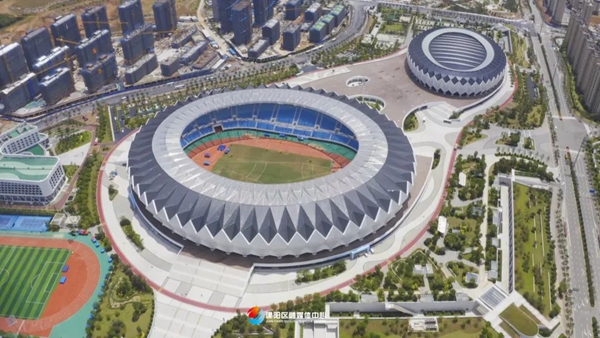詩歌與音樂相遇,長出鮮嫩的花
| 2021-02-23 11:10:10??來源:光明日報 責(zé)任編輯:肖練冰 我來說兩句 |
分享到:
|
在文學(xué)藝術(shù)的諸種門類中,沒有比詩歌與音樂更為密切的了。在人類的遠古時代,詩歌與原始音樂、原始舞蹈相伴而生。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,詩與音樂是結(jié)合在一起的。后來詩與音樂雖然分了家,但二者一直是互相滲透、互為表里的。詩歌與音樂有相近的本質(zhì),它們都表現(xiàn)人的心靈世界,都要在時間的流動中展開。 正是由于詩歌與音樂的相近與相通,所以詩人欣賞音樂,受音樂觸發(fā)進而把對音樂的感受升華為詩,就很自然了。古代詩人以詩歌描繪音樂的頗不少見,僅唐代就有錢起的《湘靈鼓瑟》、韓愈的《聽穎師彈琴》、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、李賀的《李憑箜篌引》等杰作。現(xiàn)代詩人中沈尹默的《三弦》、徐志摩的《半夜深巷琵琶》、艾青的《小澤征爾》、韓作榮的《聽桑卡彈古箏》也均是以詩歌寫音樂的名篇。 青年詩人許勁草鐘情詩歌,酷愛音樂,繼承了前輩詩人以詩歌寫音樂的傳統(tǒng),致力于音樂題材的詩歌寫作。她把自己寫音樂的詩篇收集在一起,推出了詩集《音樂女神》(中國民族文化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),這是在詩與音樂接壤地帶長出的一簇鮮嫩的花,也是詩歌與音樂相結(jié)合產(chǎn)生的寧馨兒。 詩集《音樂女神》中的作品,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,一種類型是聽樂記感,就是把自己欣賞音樂的感受用詩的意象、詩的語言傳達出來。另一種類型是音樂禮贊,即詩人對音樂作為一種藝術(shù)形式的思考、追尋與贊美。 前一種類型,聽樂記感,說來簡單,寫起來卻是頗有難度的。詩歌與音樂盡管有相通之外,但作為兩種不同的藝術(shù)門類,還是有所不同的。最重要的是藝術(shù)符號不同,音樂的符號是有規(guī)律運動的樂音,詩歌的符號是語言。樂音訴諸人們的聽覺,語言訴諸人們的想象。訴諸聽覺的樂音可以傳達歡樂、悲哀、悠閑、絕望等情緒,不受民族、地域的隔閡,因此音樂是世界通用的語言,是沒有國界的。而詩歌則由于各民族、各地域語言的差別,理解起來就沒有那么便捷。詩歌與音樂藝術(shù)符號的不同,導(dǎo)致了所傳達的信息的明確程度的不同。詩歌的符號是語言,同一種語言內(nèi),符號的能指與所指是確定的。音樂的符號是樂音,樂音既是能指又是所指,符號與實體、形式與內(nèi)容融合為一個渾然的整體。這一整體固然與主體的情緒狀態(tài)相聯(lián)系并與他的精神運動協(xié)調(diào)一致,但是它所喚起的只是一種朦朧的感覺與共鳴,這就導(dǎo)致了音樂內(nèi)涵的不確定性與多義性。即使是描繪性很強的音樂或標(biāo)題含義很具體的音樂,在聽眾心中也難于喚起明晰的概念與確切的意象。所以說,音樂是可意會不可言傳,是很難用具體的文學(xué)語言把它“翻譯”出來的。 許勁草寫這種音樂詩,就是在做這種“翻譯”工作,這是一種費力不討好的工作。因為正是由于音樂表達的不確定性,不同的聽眾之間,由于他們的生活經(jīng)驗不同,心境不同,情緒不同,就會產(chǎn)生不同的感受。許勁草傳達的感受,可能正是他們的感受,也可能偏離他們的感受。與他們感受相同的自然會頷首稱贊,與他們感受不同的就難免蹙眉不語了。不過,即使是面對后者,許勁草的詩歌也依然有其存在的價值,因為它起碼表示了樂曲“多義”中的一義,它在召喚著更多的聽眾來做出自己的詮釋。 欣賞音樂,有賴于主體的審美心理結(jié)構(gòu)。對于非音樂的耳朵,最美的音樂也沒有意義。鑒于當(dāng)下,“非音樂的耳朵”還普遍存在,國家大劇院經(jīng)常請專業(yè)人員做音樂普及的工作。許勁草所寫的音樂詩,實際也有個閱讀對象的問題。如果讀者是音樂內(nèi)行,那么對她所描繪的音樂內(nèi)涵,可能會有先得我心之感。但如果是音樂外行,那么閱讀起來也就難于有所共鳴、有所會心了。考慮到讀者的實際情況,作者特意設(shè)置了“藝術(shù)小貼士”,即對所寫的名曲、名家及著名演出團體等進行必要的背景介紹,這既點明了作者詩思的由來,也有助于讀者對音樂自身及詩的理解。 |
相關(guān)閱讀: